
1、沈从文:谈写游记
沈从文:谈写游记
写游记象是件不太费力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总有机会在作文本子上留下点成绩。至于一个作家呢,只要他肯旅行,就自然有许多可写的事事物物搁在眼前。情形尽管是这样,好游记可不怎么多。编选高级语文教本的人,将更容易深一层体会到,古今游记虽浩如烟海,入选时实费斟酌。
古典文学游记,《水经注》已得多数人承认,文字清美。同样一条河水,三五十字形容,就留给人一个深刻印象,真可说对山水有情。但是不明白南北朝时代文字风格的读者,在欣赏上不免有隔离。《洛阳伽蓝记》文笔比较富丽,景物人事相配合的叙述法,下笔极有分寸,特别引人入胜,好处也容易领会些。宋人作《洛阳名园记》,时代稍近,文体又平实易懂,记园林花木布置兼有对时人褒贬寓意,可算得一时佳作。叙边远外事如《大唐西域记》、《岭外代答》和《高丽图经》诸书,或直叙旅途见闻,或分门别类介绍地方物产、制度、风俗人情,文笔条理清楚,千年来读者还可从书中学得许多有用知识。从这些各有千秋的作品中,我们还可得到一种重要启示:好游记和好诗歌相似,有分量作品不一定要字数多,不分行写依然是诗。作游记不仅是描写山水灵秀清奇,也容许叙事抒情。读者在习惯上对于游记体裁的要求不苛刻,已给作者用笔以极大方便和鼓励。好游记不多另有原因。“文以载道”,在旧社会是句极有势力的话,把古代一切作家的思想都笼罩住了。诗歌、戏剧、小说虽然从另一角度落笔,突破限制,得到了广大群众。然而大多数作者,还是乐于作卫道文章,容易发财高升。个人文集,也总是把庙堂之文放在最前面。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着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
写游记必临水登山,善于使用手中一支笔为山水传神写照,令读者如身莅其境,一心向往,终篇后还有回味余甘,进而得到一种启发和教育,才算是成功作品。这里自然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作者得好好把握住手中那支有色泽、富情感、善体物、会叙事的笔。他不仅仅应当如一个优秀山水画家,还必需兼有一个高明人物画家的长处,而且还要博学多通,对于艺术各部门都略有会心,譬如音乐和戏剧,让主题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存在时,动静之中似乎有些空白处,还可用一种恰如其分的乐声填补空间。这个比方可能说得有点过了头,近乎夸诞玄远。不过理想文学佳作,不问是游记还是短篇小说,实在都应当给读者这么一种有声有色鲜明活泼的印象。如何培养这支笔,是一个得商讨待解决的问题。
近三十年来,报刊杂志中很有些特写式游记,写国内新人、新事、新景物,文字素朴,内容扎实,充满一种新的泥土生活气息,却比某些性质相同的短篇小说少局限性,比某些分析探讨的论文具说服力。有的作者并非职业作家,因此不必受文学作品严格的要求影响,表现上得到较大的自由。又有些还刚离开大学不久,最多习作机会还不过是学生时代写写情书或家信,就从这个底子上进行写作,由于面对的生活丰富,问题新鲜,作品给读者印象却自然而亲切。我也欢喜另外一种专家学者写成的游记,虽引古证今,可不落俗套,见解既好,文笔又明白畅达,当成史地辅助读物,对读者有实益。好游记种类还多,上二例成就比较显着。另外还有两种游记,比较普通常见:一为报刊上经常可读到的某某出国海外游记,特殊性的也对读者起教育作用,一般性的或系根据导游册子复述,又或虽然目击身经,文字条件较差,只知直接叙事,不善写景写人,缺少文学气氛,自然难给读者深刻印象。另一种是国内游记,作者始终还不脱离写卷子的基本情绪,不拘到什么名胜古迹地方去,凡见到的事物,都无所选择,一一记下。正和你我某一时在北海大石桥边、颐和园排云殿前照相差不多,虽背景壮丽,天气又十分温和,人也穿着得整齐体面,还让那位照相师热情十分的反复指点,直到装成微笑态,得到照相师点头认可,才“巴达”一下,大功告成。可是相片洗出看看,照例主题背景总是呆呆的,彼此相差不多,近于个人纪念性记录,缺少艺术所要求的新鲜。
本人即或以为逼真,他人看来实在不易感动。这种相成天有人在照,同样游记也随时有人在写,虽和艺术要求有点距离,却依旧有广大读者。由于在全国范围内舟车行旅中,经常有大量群众,都需要阅读报刊,这种游记有一定群众基矗还有一种不成功的游记,作者思想感情被理论上几个名辞缚得紧紧的,一动笔老不忘记教育他人;文思既拙滞,却只顾抄引格言名句,盼望人从字里行间发现他的哲理深思,形成一种自我陶醉。其实严肃有余,枯燥无味,既少说服力,也少感染力,写论文已不大济事,作游记自然更难望成功。
写游记除“阿丽思”女士的幻想旅行作品不计,此外总得有点生活基矗不过尽管有丰富新鲜生活经验,如没有运用文字的表现力,又缺少对外物的锐敏感觉,还是不成功。不拘写什么自然总是无生气,少新意,缺少光彩。他的毛病正如一个不高明的作曲家,仅()记住些和声原理,五线谱的应用却不熟悉,一切乐器上手也弹不出好声音。即或和千年前唐玄宗一样,居然有机会梦游天宫,得见琼楼玉宇间那群紫绡仙子,在翠碧明蓝天空背景中清歌曼舞,乐曲舞艺都佳妙无比,并且人醒回来时,印象还十分清楚明白,可是想和唐玄宗一样,凭回忆写个《紫云回》舞曲,却办不到作不好。原因是手中没有得用工具。补救方法在改善学习,先作个好读者。其次是把文字当成工具好好掌握到手中,必需用长时期“写作实践”来证实“理论概括”,绝不宜用后者代替前者,以为省事。写游记看来十分简单,搞文学就绝不能贪图省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
2、沈从文:遥夜

沈从文:遥夜
一
我似乎不能上这高而危的石桥,不知是哪一个长辈曾像用嘴巴贴着我耳朵这样说过:“爬得高,跌得重!”究竟这句话出自什么地方,我实不知道。
石桥美丽极了。我不曾看过大理石,但这时我一望便知道除了大理石以外再没有什么石头可以造成这样一座又高大、又庄严、又美丽的桥了!这桥搭在一条深而窄的溪涧上,桥两头都有许多石磴子;上去的那一边石磴是平斜好走的,下去的那边却陡峻笔直。我不知不觉就上到桥顶了。我很小心地扶着那用黑色明角质做成的空花栏杆向下望,啊,可不把我吓死了!三十丈,也许还不止。下面溪水大概是涸了,看着有无数用为筑桥剩下的大而笨的白色石块,懒懒散散睡了一溪沟。石罅里,小而活泼的细流在那里跳舞一般的走着唱着。
我又仰了头去望空中,天是蓝的,蓝得怕人!真怪事!为甚这样蓝色天空会跳出许许多多同小电灯一样的五色小星星来?它们满天跑着,我眼睛被它光芒闪花了。
这是什么世界呢?这地方莫非就是通常人们说的天宫一类的处所吧?我想要找一个在此居住的人问问,可是尽眼力向各方望去,除了些葱绿参天的树木,柳木根下一些嫩白色水仙花在小剑般淡绿色叶中露出圆脸外,连一个小生物——小到麻雀一类东西也不见!……或是过于寒冷了吧!不错,这地方是有清冷冷的微风,我在战栗。
但是这风是我很愿意接近的,我心里所有的委屈当第一次感受到风时便通给吹掉了!我这时绝不会想到二十年来许多不快的事情。
我似乎很满足,但并不像往日正当肚中感到空虚时忽然得到一片满涂果子酱的烤面包那么满足,也不是像在月前一个无钱早晨不能到图书馆去取暖时,忽然从小背心第三口袋里寻出一枚两角钱币那么快意,我简直并不是身心的快适,因为这是我灵魂遨游于虹的国,而且灵魂也为这调和的伟大世界溶解了!
——我忘了买我重游的预约了,这是如何令人怅惘而伤心的事!
二
当我站在靠墙一株洋槐背后,偷偷的展开了心的网幕接受那银筝般歌声时,我忘了这是梦里。
她是如何的可爱!我虽不曾认识她的面孔便知道了。她是又标致、又温柔、又美丽的一个女人,人间的美,女性的美,她都一人占有了。她必是穿着淡紫色的旗袍,她的头发必是漆黑有光,……我从她那拂过我耳朵的微笑声,攒进我心里清歌声,可以断定我是猜想的一点不错。
她的歌是生着一对银白薄纱般翅膀的:不止能跑到此时同她在一块用一块或两三块洋钱买她歌声的那俗恶男子心中去,并且也跑进那个在洋槐背后胆小腼腆的孩子心里去了!……也许还能跑到这时天上小月儿照着的一切人们心里,借着这清冷有秋意夹上些稻香的微风。
歌声停了。这显然是一种身体上的故障,并非曲的终止。我依然靠着洋槐,用耳与心极力搜索从白花窗幕内漏出的那种继歌声以后而起的窸窣。
“口很……!这是一种多么悦耳的咳嗽!可怜啊!这明是小喉咙倦于紧张后一种娇惰表示。想着承受这娇惰表示以后那一瞬的那个俗恶厌物,心中真似乎有许多小小花针在刺。但我并不即因此而跑开,骄傲心终战不过妒忌心呢。
“再唱个吧!小鸟儿。”像老鸟叫的男子声撞入我耳朵。这声音正是又粗暴又残忍惯于用命令式使对方服从他的金钱的玩客口中说的。我的天!这是对于一个女子,而且是这样可爱可怜的女子应说的吗?她那银筝般歌声就值不得用一点温柔语气来恳求吗?一块两三块洋钱把她自由尊贵践踏了,该死的东西!可恶的男子!
她似乎又在唱了!这时歌声比先前的好像生涩了一点,而且在每个字里,每一句里,以及尾音,都带了哭音;这哭音很易发见。继续的歌声中,杂着那男子满意高兴奏拍的掌声;歌如下:
可怜的小鸟儿啊!
你不必再歌了吧!
你歌咏的梦已不会再实现了。
一切都死了!
一切都同时间死去了!
使你伤心的月姐姐披了大氅,不会为你歌声而甩去了,同你目语的星星已嫁人了,玫瑰花已憔悴了——为了失恋,水仙花已枯萎了——为了失恋。
可怜的鸟儿啊!
你不必——请你不必再歌了吧!
我心中的温暖,
为你歌取尽了!
可怜的鸟儿啊!
为月,为星,为玫瑰,为水仙,为我,为一切,为爱而莫再歌了吧!
我实在无勇气继()续的听下去了。我心中刚才随歌声得来一点春风般暖气,已被她以后歌声追讨去了!我知道果真再听下去,定要强取我一汪眼泪去答复她的歌意。
我立刻背了那用白花窗幔幕着的窗口走去,渺渺茫茫见不到一丝光明。心中的悲哀,依然挤了两颗热泪到眼睛前来……被角的湿冷使我惊醒,歌声还在心的深处长颤。
一九二四年圣诞节后一日北京作
3、沈从文:情书

沈从文:情书
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
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
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
永远不会老去,
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
我想到这些,
我十分犹豫了。
生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
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
用对自然倾心的眼,
反观人生。
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
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
在同一人事上,
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
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
我也安慰自己过,
我说: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4、沈从文:论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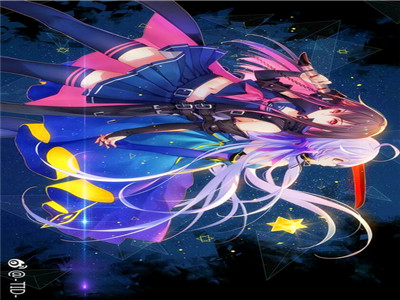
沈从文:论技巧
几年来文学词典上有个名词极不走运,就是“技巧”。多数人说到技巧时,就有一种鄙视意识。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极害羞,在人面前深怕提这两个字。“技巧”两个字似乎包含了纤细、琐碎、空洞等等意味,有时甚至于带点猥亵下流意味。
对于小玩具小摆设,我们褒奖赞颂中,离不了“技巧”一词,批评一篇文章,加上“技巧得很”时,就隐寓似褒实贬。说及一个人,若说他“为人有技巧”,这人便俨然是个世故滑头样子。总而言之,“技巧”一字已被流行观念所限制,所拘束,成为要不得的东西了。流行观念的成立,值得注意,流行观念的是非,值得讨论。
《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觉得极有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骈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章写得十分老到,毫无可疑,也在技巧。前者具永久性,因为注重安排文字,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亲切,妥贴,近情,合理的目的。后者无永久性,因为除了玩弄文字以外毫无好处,近于精力白费,空洞无物。
同样是技巧,技巧的价值,是在看它如何使用而决定的。
一件恋爱故事,赵五爷爱上了钱少奶奶,孙大娘原是赵五爷的宝贝,知道情形,觉得失恋,气愤不过,便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了。同样这么一件事,由一个新闻记者笔下写来,至多不过是就原来的故事,加上死者胡同名称,门牌号数,再随意记记屋中情形,附上几句公子多情,佳人命薄,……于是血染茵席,返魂无术,如此如此而已。可是这件事若由冰心女士写下来,大致就不同了。记者用的是记者笔调,可写成一篇社会新闻。冰心女士懂得文学技巧,又能运用文学技巧,也许写出来便成一篇杰作了。从这一点说来,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
同样这么一件事,冰心女士动手把它写成一篇小说,称为杰作;另外一个作家,用同一方法,同一组织写成一个作品,结果却完全失败。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作品的成败,是决定在技巧上的。
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贴”,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贴,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假定有一个人,在同一主题下连续写故事两篇,一则马马虎虎,信手写下,杂凑而成;一则对于一句话一个字,全部发展,整个组织,皆求其恰到好处,看去俨然不多不少。这两个作品本身的优劣,以及留给读者的印象,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一个懂得技巧在艺术完成上的责任的人,对于技巧的态度,似乎应当看得客观一点的。
也许有人会那么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其一是文字经济,不浪费,自然,能亲切而近人情,有时虽有某些夸张,那好处仍然是能用人心来衡量,用人事作比较。至于矫揉造作,雕琢刻画的技巧,没有它,不妨事。”请问阁下:能经济,能不浪费,能亲切而近人情,不是技巧是什么?所谓矫揉造作,实在是技巧不足;所谓雕琢刻画,实在是技巧过多。是“不足”与“过多”的过失,非技巧本身过失。
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猥琐的骈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虽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技巧被诅咒,被轻视,同时也近于被误解,便因为,一,技巧在某种习气下已发展过多,转入空疏;二,新时代所需要,实在不在乎此。社会需变革,必变革,方能进步。徒重技巧的文字,就文字本身言已成为进步阻碍,就社会言更无多少帮助。技巧有害于新文学运动,自然不能否认。
惟过犹不及。正()由于数年来技巧二字被侮辱,被蔑视,许多所谓有思想的作品企图刻画时代变动的一部分或全体,在时间面前,却站立不住,反而更容易被“时代”淘汰忘却了。
一面流行观念虽已把技巧二字抛入毛坑里,事实是,有思想的作家,若预备写出一点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读者注意,推动社会产生变革,作家应当作的第一件事,还是得把技巧学会。
目前中国作者,若希望把本人作品成为光明的颂歌,未来世界的圣典,既不知如何驾驭文字,尽文字本能,使其具有光辉,效力,更不知如何安排作品,使作品产生魔力,这颂歌,这圣典,是无法产生的。
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因为艺术同技巧原本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作
